近日,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籍《中华戏剧通史简编》。这是一部突破传统叙事框架、勇于开拓、气象万千的戏剧史新编,以“上下延伸,横向融通”的新视野重新审视中华戏剧史,将其源流娓娓道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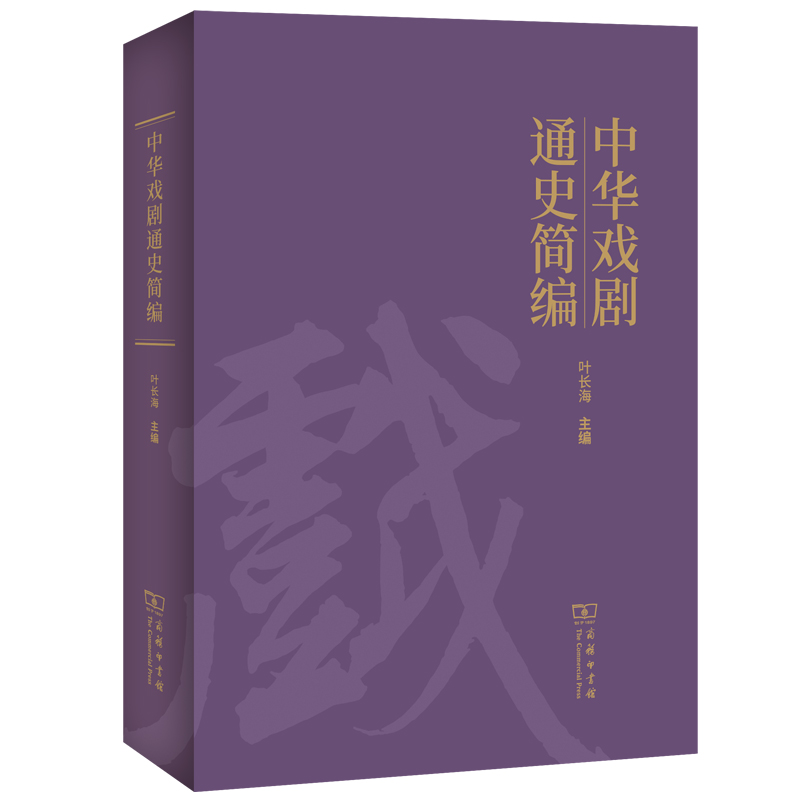
本书用戏剧学的理念诠释中国历史上繁复的演剧现象,用民族学的眼光发现中华大家庭中各民族戏剧文化的特点及其意义,用历史分析方法关注各个不同时期各种戏剧现象的独特性及其有机联系;全书通过灵活的章节设计以及点面互应、繁简结合的书写方式,力求以有限的篇幅全面包容“中华”各民族古往今来的各种“戏剧”,以此来体现“通史”的意义。
全书将中华戏剧的悠久历史分为三编来展示。上编“源流演变”阐述远古至五代戏剧史;中编“古典盛世”阐述宋元明清戏剧史;下编“多元拓展”阐述近现代戏剧史。
作者简介
叶长海,1944年生,浙江永嘉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戏剧学史稿》《曲学与戏剧学》《王骥德〈曲律〉研究》《汤学刍议》《读书谈艺》等。曾获首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1984年)、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年)、首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1999年)等。
精彩试读
模仿是人类的天性,是学习的基本方式,也是游戏的重要手段。这种天性可以追溯到哺乳动物的其他物种,也可以在人类的儿童行为中得到印证。比如观察儿童的活动可以发现,模仿游戏是其生活乐趣的重要来源,而常见的儿童游戏也表现了明显的戏剧倾向。“过家家”“客人来访”“哺育洋娃娃”都是这种具有戏剧倾向的模仿游戏。《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载的“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也说明扮演是模仿游戏的重要手段;一旦在游戏中通过扮演而产生角色,那么模仿就会导致戏剧的发生。
通过“戏”这个字,我们看出装扮游戏与戏剧的关系。“戏”字原指军队的侧翼或偏师;又假借为“麾”,指军中的帅旗。另外,它还是兵器的名称。由于兵器用于战争,战争是使用武力进行的比赛和斗争,所以“戏”又有“角力”“角斗”之义;再引申,就有嬉戏、游戏、戏弄、戏谑等义,以及歌舞、杂技等表演义。也就是说,在“戏”字的内涵发展史上,游戏的含义早于戏剧的含义。由于古人往往在游戏中采用扮演的手段,所以在“戏”字当中有游戏义与戏剧义的并存。比如《史记·周本纪》记载:“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
关于成人的装扮游戏,《搜神记》有一则记载,说汉灵帝曾在宫中做过一种游戏。他让宫女在西园中装扮成客栈主人,他自己身穿旧衣,扮成旅客,“行至舍间,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在这里,皇帝摇身一变成为普通的旅人,与卑贱的宫女“共饮食”。前文说过,这种游戏的奥妙在于:游戏者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转化自己的社会角色。
同其他早期形态的戏剧相比,游戏戏剧比较轻松。不过,它仍然有其规则。在少数民族的游戏戏剧中,这种规则往往来源于古老仪式。比如跳虎节中的虎抱蛋、虎抢蛋等,既有娱乐性,又反映了某种信仰。下面介绍的“大头和尚戏柳翠”,就属于这种游戏戏剧。
“大头和尚戏青柳”是在云南省晋宁县夕阳乡打黑村等地流行的哑剧。剧中有两个人物,一是大头和尚,面具为肥硕的红脸和尚;一个是青柳,面具为美貌的年轻女子。大头和尚白衣黑裤;青柳着蓝色上衣,左裤腿为白色,右裤腿为红色。表演过程中用节奏缓慢的锣鼓乐伴奏。驼背腆腹的大头和尚和扭动腰肢的青柳先后出场。和尚欲调戏青柳,青柳不从。和尚拍拍腰间的钱袋,示意自己很有钱。于是青柳作顺从之态,为其端上茶水,又为之点烟捶背。和尚作舒心状。青柳又为其端上洗脸水和毛巾。和尚洗后,青柳又端上洗脚水。和尚嫌烫,打了青柳一记耳光。青柳重新打水,和尚洗濯之后非常满意,于是搂着青柳的腰扭动着下场。全剧历时约十五分钟,情节简单,就像一场游戏。
但这出戏却有悠久的历史。村民说,“大头和尚”的历史与“跳猫猫”一样的久远。而且,我们知道,明代已有戏剧“大头和尚戏柳翠”(又称“耍和尚”或“大头和尚”),以及民间故事“月明和尚度柳翠”。徐渭曾把这一故事写成杂剧,属于《四声猿》之一。元明清三代的民间社火中均有这一表演。至今山西五台山一带还有这一节目。可以肯定,打黑村的大头和尚与北方的大头和尚有联系。也就是说,“大头和尚”是一出从汉族居住区流传到打黑村的剧目。
关于上述联系,另外有一出戏可以作为旁证。这就是流行于楚雄州元谋县的“大头宝宝戏柳翠”。它属于花灯传统歌舞,是元谋县多克村乐春社每年必演的头场灯戏。其情节是:清晨,柳翠开窗扫屋,然后梳妆打扮,叫来大头宝宝。大头宝宝观看字画和屋内陈设,夸赞柳翠能干。柳翠让大头宝宝洗脸,他洗不干净,柳翠只好帮他洗。二人梳洗完毕,大头宝宝烧香叩头,求神保佑。接下来便是猴子、柳翠、大头宝宝、狮子戏耍舞蹈。剧中用扇子作道具,表演洒、扫、挂画、梳妆、洗脸等动作,并运用了“加官”“筋斗”等毯子功。全场用打击乐伴奏,有《长板》《碎板》《二三板》等乐曲。根据徐朔方的介绍,明代杂剧《月明和尚度柳翠》有《新水令》曲,有柳翠在前世诱惑玉禅师、今世由月明和尚度脱的情节。尽管“大头和尚戏青柳”既不同于“大头宝宝戏柳翠”,也不同于《月明和尚度柳翠》,各是一出戏;但其中的相似性不容忽视。也就是说,从明代的“月明和尚”到现今云南的“大头和尚”,其间必然有着源与流的关系。
以上几出戏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在云南这块特定的文化土壤中,游戏化是情节复杂的故事戏的发展趋向。限于篇幅,本书对此未能一一介绍。不过,读者不妨自行了解一下云南巍山彝族人的“叫地脉”“叫饭魂”和“花子闹房”、楚雄姚安彝族人的儿童戏“嘎勒庄”、云南巍山汉族人的“骑火驴”、大理云龙白族的婚礼表演“耳支歌”(“哑巴戏”)、贵州荔波布依族人的傩戏“戏弄外家”。这些戏都有鲜明的游戏性,或者说有散乐渊源。其功能,尽管也表现为规劝、谏诤、传授知识和加强集体感,但主要在于让参加者通过扮演活动而使情绪得到宣泄。后世戏剧的娱乐传统,应该就是通过这种游戏戏剧奠定的。
南方网、粤学习记者 朱绮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