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作《论境界:〈人间词话〉与康德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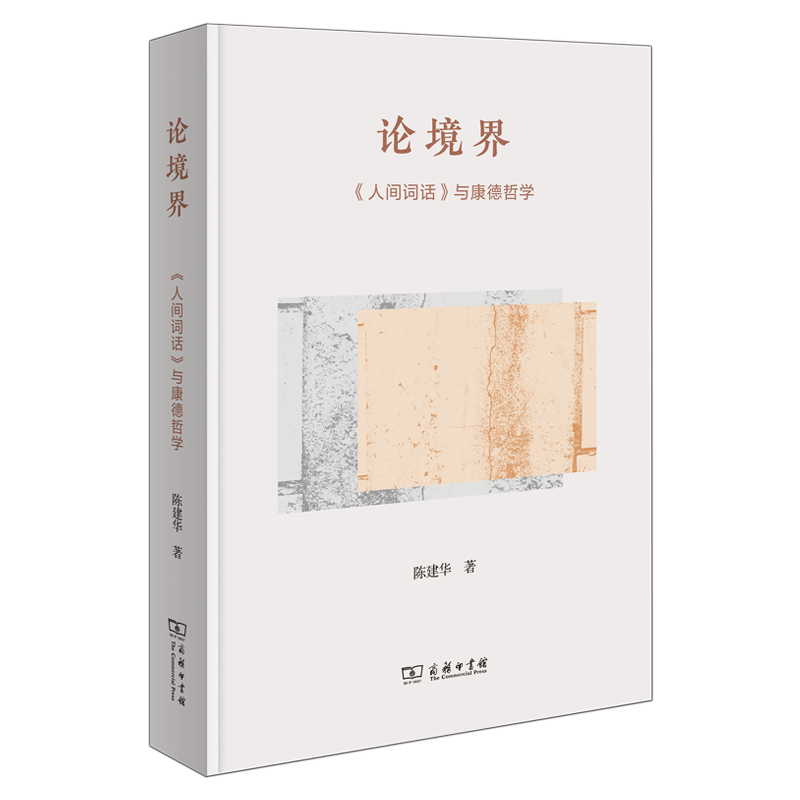
为什么《人间词话》经久不衰?它的现代性奥秘又在哪里?本书中,作者陈建华教授使用实证与历史脉络化方法,在王国维与康德哲学的整体构架中解读《人间词话》,指出它由于西方哲学与本土诗学的融合、碰撞而趣味横生,歧义纷纭,其中的“境界”说核心则是一种新的科学世界观,含有欧洲启蒙思想的个人主义与理性精神。
本书由三篇文章组成,读者可循序渐进体味王国维由叔本华转向康德哲学的经历,进一步了解王国维与康德哲学、时代及清末文论的生产场域的关系,从整体上来观照,深入到尘封的历史断面而发现幽微之处。
作者简介
陈建华,生于上海。复旦大学、哈佛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复旦大学、美国欧柏林学院、上海交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现为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文学文化史、“革命”观念史、诗学诠释学、视觉文化史、中国电影史、近现代报刊与传播文化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等。著有Revolution and Form: Mao Dun’s Early Novels and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ty,From Revolution to the Republic: Chen Jianhua on Vernacular Chinese Moder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以及《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李欧梵教授访谈录》《帝制末与世纪末——中国文学文化考论》《雕笼与火鸟(三十年集)》《古今与跨界——中国文学文化研究》《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史》《陆小曼·1927·上海》《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词曲中的中国》《爱与真的启示——张爱玲的晚期风格》《摩登图释》。另有文学创作《去年夏天在纽约》《陈建华诗选》《乱世萨克斯风》《灵氛回响》《凌波微语》《午后的繁花》《风义的怀思》等。
试读章节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管是谁说的,这句话很能传达当下互联网时代的阅读风尚。这对王国维也适用,至少对现代经典的《人间词话》而言,他的生命的悲剧性也不亚于那位丹麦王子。话虽这么说,阅读的自由有一定的限度,似乎谁也不会把哈姆雷特或是王国维读成喜剧,而且阅读中个人三观与时代风气、教育背景或朋友圈影响等因素息息相关。回想20世纪80年代,跟现在大不一样,一本书动辄印数上万册,那种大众阅读的狂欢景象,形成某种公共记忆的东西,至今令人神往。在我们的阅读记忆中,印刻着李泽厚先生。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断言:“王国维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浸染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唯心主义。”或如陈元晖的《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一书等,皆流行一时,长期以来几乎主导了《人间词话》的阅读史,王国维的悲剧生命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被拧成一个死结,坚不可破。
2019年5月我在《书城》上发表了《〈人间词话〉的现代转向》一文,其实是宋词研究系列的一个迂回插曲。我想在中国韵文抒情传统中彰显宋词的某种纯艺术特点,而《人间词话》对姜夔的批评触及“形式”问题,觉得有必要讨论一下,结果却给自己留下一个挥之不去的悬念。《人间词话》实在重要,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形塑了我们对文学发展的看法,哲思隽言滋养了我们的审美趣味,其“经典化”过程也是批评史上的一个奇观。
文中说:“王国维在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深受叔本华悲剧观的影响。《人间词话》发表于1908年,其中的认识论则渊源于康德。”这表述看似波澜不惊,但标出前后年份蕴含着我的历史化研究取向,即认真看待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里对叔本华的缺乏“客观”的质疑并由此转向康德哲学,其中“认识论”扮演了主角,这对《人间词话》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起点。以往学者大多阐述王国维“以我观物”“以物观物”及“隔”与“不隔”等美学创见,皆认为主要是受了叔本华的影响。我的文章则从“显象”—康德认识论的基点—出发,专注于“自然”的“写实”主张,并和“隔”与“不隔”以及对南宋词的排斥的观点联系起来,指出整体上这是个“世界观”问题,背后站着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的科学实证主义,在反对形式主义与简约传统方面显示出某种“现代性”走向。
在这么思考时,我的记忆库存被激活,思想碎片从各个角落跑了出来,交互产生化学反应。我一向关注晚清文学与图像的“逼真”观念,这涉及文学上“写实主义”模式的近代系谱,《点石斋画报》是个显例。图像基本采用透视法,与照相、石印技术联袂而至,英人美查鼓吹“逼肖”表现外在世界的优越性,可说此是一次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输入,却前所未有地展示了城市与人的种种奇观。康德的知识论中,经验世界在人心的“显象”是其哲学基点,根源于柏拉图的“摹仿”理论,这一点反而是叔本华强调了康德对西方哲学的贡献。王国维并未解释“再现”概念,而他要求“写实”与“自然”对应,并限于对“情”“景”的描绘,以及基于“隔”与“不隔”的批评对南宋词的排斥,这几点构成他的“境界”说的基本框架,且强调“真”“伪”价值的二元判断。因此我认为这属于一种较为有限的“再现”理论,意识形态上与晚清的“照相写实主义”是殊途同归的。
王国维主张“自然”“写实”,意在针砭清末词风,但他对南宋词的贬斥,从“现代性”角度说是对传统的“简约化”做法。有人把《人间词话》中反对用典等观点与胡适的“八不主义”相联系,这种比较流于表面,我想到的是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对中国文人画的批评,认为明清画家讲究“气韵”的笔墨意趣,发展出烦琐的审美套式,只具区域性美学意趣而缺乏普适价值。这一西方“现代”偏见在后现代境遇中被翻转,如诺曼·布列逊在《视阈与绘画》一书中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提香与北宋的巨然并置,认为他们分别代表了西东方“凝视”与“瞥视”的视觉性范式。
列文森的偏见是一回事,某种意义上这似乎也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自然过程。与儒家的现代命运相似,中国的山水画不再讲求皴法之类的笔墨意趣而趋向写实主义。传统在近现代处处发生断裂,不光是绘画。张爱玲的《更衣记》一文讲服装的古今变迁,中国古代服装充塞着有闲阶级才能欣赏的繁缛的图案与无意义的点缀品,到清末发生突变,出现紧身窄袖等样式,因此她总结:“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这跟皴法的消失是同样的道理。
这篇文章的思考基本上是直观性质的,但时过未境迁,此后做过讲座,或在课堂上讨论,均从“现代转向”或“视觉转向”的角度。直至去年(2021)夏天,部分出于学生们的鼓动,着手论文的写作,进一步挖掘王国维与康德哲学、时代及清末文论的生产场域的关系,萦绕脑中的是:为什么《人间词话》经久不衰?它的现代性奥秘在哪里?实际上与历史化探究平行的方法是回放历史的方法,如德塞都所言,文本在阅读史中呈现其意义,或如麦克罗汉所说.“由效果出发追溯原因”。这对于建立问题意识至关重要,有助于研究中始终不忘整体观照,避免碎片化,且深入到尘封的历史断面而发现幽微之处。
这一场自我论证之旅迂回曲折,一波三折,所谓终点即起点,有的地方可说是从头开始。比如我原先使用的是周锡山教授编的《王国维集》,而学术论述按照文献使用的严格规范将引用文本恢复《教育世界》的原貌,更要紧的是必须面对该杂志上登刊的有关康德的署名和未署名文本,这些至今仍存在争议。尽管佛雏、陈鸿祥等学者对它们做了辨正工作,证明皆为王国维所作,周锡山编入全集,也加强了佐证,但对我来说必须躬身为之,搭建一个自觉心安的批评屋架。我大概较为保守,取具体甄别的态度,从最早介绍康德的《汗德之知识论》入手,有学者考证这篇未署名之文译自日人著作,但我觉得王国维作为主编刊发此文,显示一定的倾向性。他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指斥梁启超对康德哲学的介绍,在《教育世界》上的《汗德之知识论》即为纠正之作,又在《论性》中肯定并运用了“知识论”,由是可说明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掌握程度,我想这样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以此为突破口,对有关康德的各篇文章做考察,以署名文章为据,与未署名文章相参证,探寻王国维与康德哲学的关系。事实上在稍早于《红楼梦评论》的《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中已提出了康德的伦理学原则,并贯穿于《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与《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等文中。正如他在1907年《自序》中说“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表明他费时数年四度钻研康德的三大批判,最终达到某种整体性把握,这跟我对他的思想追踪的结果是一致的。尤其自1906年起转向文学而发表了《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人间词》甲乙稿序等文,可见他是如何基于中国文艺的历史运用康德哲学,并与之商榷或加以调适,这种本土化的过程充满复杂张力,终于在《人间词话》中体现为“七宝楼台”似的意象批评——一种原创美学形式的结晶。
说王国维受康德的影响并不新鲜,近年来也有学者把康德美学与《人间词话》相链接,不同的是我主要使用实证与历史脉络化方法,在他与康德哲学的整体构架中解读《人间词话》,指出它由于西方哲学与本土诗学的融合、碰撞而趣味横生,歧义纷纭,而“境界”说的核心则是一种新的科学世界观,含有欧洲启蒙思想的个人主义与理性精神。这不仅合乎王国维以美育造就完美国民人格的教育理想,也预示中国的现代性方向。的确,在美学上他受到叔本华的影响,学者们在这方面所获成果甚丰。不过就其知识论基础而言,叔本华完全来自康德,王国维也经由叔本华“上窥”康德,且更强调审美实践中的伦理价值,遂与叔本华拉开了距离。他特别欣赏叔本华的“直观”理论,并体现在《人间词话》与《人间词》中。照一般说法,尼采与叔本华的哲学大大张扬了人的主观精神,开启了西方的非理性思想与现代主义文艺潮流,而在王国维那里,对经验世界则持保留态度,感情受制于理性而处于被规训的地位。
南方网、粤学习记者 朱绮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