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画家、文化学者冯骥才荣膺2021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杰出作家”。“年度杰出作家”是南方文学盛典最具分量的一项荣誉,用以致敬对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写作者。冯骥才凭借202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们》摘得这一桂冠。
10月23日,由南方都市报发起主办,佛山市顺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顺德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顺德区北滘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1南方文学盛典”在顺德北滘文化中心音乐厅隆重举办。备受瞩目的“2021南方文学盛典”六项荣誉——年度杰出作家、年度小说家、年度诗人、年度散文家、年度文学评论家、年度最具潜力新人逐一揭晓,百余名作家、学者、文学爱好者和顺德本地读者共襄盛举。
*年度杰出作家冯骥才
祖籍浙江宁波,1942年生于天津,中国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现任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协名誉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他是“伤痕文学”代表作家,其“文化反思小说”在当今文坛影响深远。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二百余种。代表作《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一百个人的十年》《俗世奇人》《单筒望远镜》《艺术家们》等。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韩、越等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五十余种。多次在国内外获奖。他倡导与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传统村落保护等文化行为对当代人文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冯骥才
*授奖辞
冯骥才是一个名字,也是一种文化情怀。他向艺术要美,向俗世要传奇,向行将消逝的文化遗产和古村落要文明的证据,向过去要未来。他对文化现状倾全力而赴之的痛惜、救护,把知识分子的良知落实成了一种有感召力的行动、有反思精神的写作。他出版于二〇二〇年度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们》,是对一种文化人格的追念和加冕。时代炽热,才华闪光,那些艺术家的世界里,欲望与理想同行,绝望与希望并存,但在浮华背后,记忆最重要的遗存仍然是对美和真理的求索,对善好人世的眷恋。这本写给自己的庄重之书,也充盈着对精神同道的真诚礼赞。
*冯骥才答谢辞:
感谢两个字是首先要说的。它并非虚言,而是我个人由衷的表达。
一个有影响的重要的文学奖对于作家来说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使你得到一种肯定,来自专家和学者的肯定;我把评委们撰写的颁奖词,看做是给我最好的思想礼物,它有利于我的自省与自我的思辨。有助于我下边的写作。
另一个是给我带来更多读者的阅读。作家的作品是在读者的阅读中活着的。我一直以为,作品的生命由再版开始,如果一本书不再出版,没有下一代读者,作品的生命就会完结。当然,任何文学奖都不可能提高作品的质量,但它可以唤起读者对我们的作品产生阅读的兴趣。愈有影响的文学奖,这种效应愈大。
所以,我今天是幸运的。
我个人的写作史分做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始于上世纪八十代的新时期。我做过十几年的职业作家。此后,由于我认为“抢救濒危的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比我个人写作更重要,我自愿放下写小说的笔,投身到田野大地中。在长达二十五年里,我更多的写作是和消费时代功利主义的反文化的思潮作战,为建立遗产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倾尽全力,还有大量的田野档案的编制。
近几年,由于年岁大了,难于再去田野奔波,在书房里的时间多了,为什么小说迎头找上了我?
我的体验是,一个人一旦与文学扰在一起,就会被纠缠终生,永世难分。你的文学立场就是你生活的立场,你对生活的感受方式常常是文学的感受方式,你的生活思维也融合了文学的思维。
生活,大多是在不经意中积淀下来的。在我二十多年的不写小说的时间里,我心中的文学却在成长。同时,在文化抢救中,我对大地上的人、生活、时代、历史、文明的理解大大地加深。既是意韵的加深,也是思想的加深。当我再度拿起笔来,便有了“不一样的人物、不一样的思考、不一样的小说”的感觉。当我把这些“心中的文学”写出来后,我不知道读者的看法。我曾经的一代读者离我遥远,当今的读者会不会与我彼此陌生?
故此,我把今日南方文学盛典颁发的奖,看做是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使我在面对当今这个茫茫的读者世界时,有了一些信心。作家的天职是为读者工作。通过文字与读者一同认知生活与时代、寻找温暖与光,以及不屈不挠的力量。
为此,再次感谢评委、南方都市报,感谢大家用宝贵的时光倾听我的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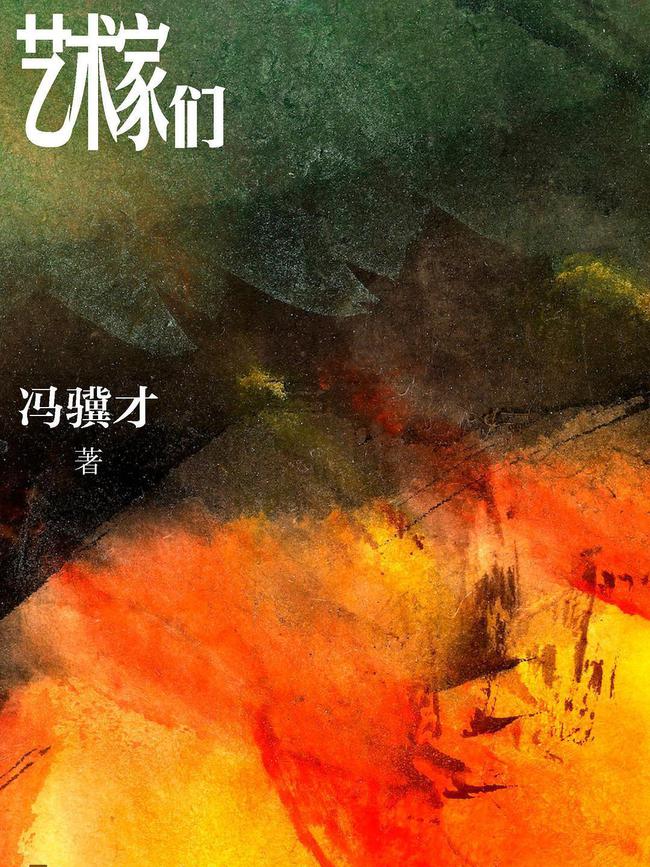
长篇小说《艺术家们》,冯骥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0月
*冯骥才访谈:文学创作对于我是不可遏制的
这本书在我心里压了太久了
南都:请谈谈动念写《艺术家们》这部小说的原因。
冯骥才:原因挺复杂的,不是一个原因导致了一个结果,而是有多重原因。实际上,年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梦想。我是画画出身,我也看过一些写艺术家的小说。这类小说中国不多,欧洲多一点,而且有写得非常好的。比如我特别喜欢罗曼·罗兰写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罗曼·罗兰写过一系列音乐家的评传,比如《贝多芬传》《亨德尔传》,也写过雕塑家米开朗琪罗的传记。
出生于上世纪40至50年代的那一代人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奉为翻译文学里的经典。因为是傅雷先生翻译的,译笔特别好。最重要的是,这是以贝多芬为原型写的一部小说,他写出了音乐家的一种主观的感觉,这种感觉充满了音乐的气质——音乐里的韵律,音乐里的节奏,音乐里的独特的意境。《艺术家们》发表以后,《收获》杂志在上海给我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我在研讨会上就提到过《约翰·克里斯多夫》。
20世纪80年代,我们那一批作家在伤痕文学之后进入文坛,写的更多的是对社会贴得很紧的,反映社会矛盾和时代气息的,反映人的渴望的小说,帮助读者认识生活。那时我很想写一个中篇,叫《艺术家生活圆舞曲》。我脑子里有很多艺术家的形象,因为我认识很多同时代的艺术家,有很多特别值得写的东西。
我想我多亏没写。如果我写,我一定会把他们写浅薄了。幸亏我又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我经历了不同的时代,经过了社会的转折,也体验了不同的时代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市场的时代,消费社会,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东西文化的激烈碰撞等。这样一些大的背景下,艺术家们各奔前程,走不同的道路,他们的命运如何?我经过了这些时代,我当然要思考艺术家的命运,他们的心灵和历史,他们在不同时代下、在各种新的问题面前的遭遇与选择,以及选择带来的不同境遇。这些都是我写《艺术家们》这部小说的原因。
南都:小说的20多万字是一气呵成的吗?
冯骥才:我写《艺术家们》这部小说时特别快。第一遍下来可能也就是两个月多一点。写完以后修改了一段时间。如果不是新冠疫情蜗居在家,这个小说根本写不了。因为我的时间特别紧张。
但疫情突然就中断了我很多联系,跟谁也不能见了。这段时间给我一个巨大的财富,就是连贯的、完整的几个月的时间。平常我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时间不连贯。写小说的人要跟他虚构的人物在一起生活。你就是跟你家人在一起,面对面,你脑子里想的也是你虚构的人。你家里人当然已经习惯你了,一般人不习惯你,觉得你怎么忽然就走神了,也不听人说话了?实际上你在跟你虚构的人物交流。虚构的人物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变化、遭遇。
对于我来讲,写短篇得要一个礼拜,写中篇我起码要二十天到一个月,写长篇就得几个月的时间。我在写《俗世奇人》的时候基本是放假和过年的时候写。写《俗世奇人》最快的时候我一天可以写两个短篇。
为什么呢?不是我本事大,而是这个东西在我心里憋的时间太长了。有时间它就会蹦出来。
但是长篇不行。写长篇必须有一段比较长的充裕的时间,而且要“与世隔绝”。整个那段时间,天赐的,全给我了,很美妙。所以我一口气就写下来了。你看这本书你一定觉得很顺畅。为什么呢?因为压得太久了,就像火山一样,岩浆压的时间越久,喷发出来的力量就越大。
有现实原型,你才好去感知他
南都:读完小说后我有一个感觉,小说前半部分楚云天的经历跟您自己人生的某些阶段十分接近,所以,这个小说里到底有哪些是取材于您的真实生活?
冯骥才:小说的人物实际都是虚构的,但一般小说的人物都有原型,特别是主要人物。如果没有原型,没有一个生命的实体,你就不好感觉他。
就是城市也有原型。比如贾平凹写商州,或者莫言写高密;就像天津是生我养我之地。王安忆写上海得心应手,因为那是生她养她的地方,她从小跟那个地方水乳交融,她的情感、她的生命的气息,跟那个地方都是沟通的。所以人物搁在那儿,自然就活了。
人物就像城市一样。城市你把它搁在一个熟悉的地方,你就好感觉它,所有地理位置、风物、环境,周围人的性格,就都是活的。如果完全虚构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你可以把你知道的地方换一个名字,但这个地方的感觉必须是你熟悉的。
人也是这样。这个人物必须有可感觉的现实依据。比如我在生活中发现那个人物和我写的人物特别接近,我就把这个人物无形中而不是有意识地写进来了,使他成为一个原型。原型的意思不是说一模一样照着他来写。作家从自己最熟悉的那些人身上去找生命最可感的东西作为原型。一些其他人物的特征,如果能跟这个角色生命融合,变成同一个个体,那自然而然也被写进来。也可能再加上作者自己的虚构。
所以你刚才那句话说得特别对,《艺术家们》上半部我的东西很多,到了下半部我的东西就很少了。上半部我主要写六七十年代的艺术青年。那个时候没有艺术事业,他们没有社会责任,但是他们有对艺术一往情深的挚爱,有艺术的梦想,美的梦想。这么一群人他们在一起抱团取暖,共同感受艺术的气息。小说里的“三剑客”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的友谊也特别珍贵,那就是我的年轻时代。
我写的时候,我周围的那些人自然而然就进来了。因为过去的生活里的记忆,总是把最让你感动的东西留存下来。那些人很容易就进入了我的小说。可能是他们的相貌,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相貌,加上他们的个性,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人的细节,或者是我想象出来的东西……自然而然就把它们放在一起了。
因为楚云天是《艺术家们》里最主要的人物,而且我想用他来表现我的角度,我要揭示我的角度,我个人就很容易带入。我把自己写进来的时候,一定带着我的经历,带着我的故事,带着我的情节,最重要的是带着我的心理和对艺术的感觉。这样,等人物都进来以后,我已经知道艺术家在新的一个时代里会如何行动。每个人会怎么做,我心里都明白。他们就“自由发展了”。
南都:所以您就像“架构师”一样,完成了前期定调的工作以后,小说就开始自由发展了。
冯骥才:说实话我根本不知道它会怎么发展。当然我有一些大概的想法。我知道我的朋友们有的沉沦了,在市场社会里,被消费社会的准则所左右了,被庸俗社会观侵蚀了,非常有才气的作家,最后崩溃了。
比如我写洛夫这个人物,我自己认识的好多艺术家,有更悲惨的自戕。什么样的都有。也有的艺术家没有那么大的才气的,时代让他开阔了眼界,激发了他的创造力,但后来也沉沦了,在生活中慢慢烟消云散了。也有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坚守艺术的,这样的艺术家特别少。比如我在小说里写了两个人,一个是高宇奇,一个是易了然。
我也写了唐三间、屈放歌,这些人都有生活原型,在市场里呼风唤雨。他们在市场上太成功了,有那种大老板式的财大气粗。在市场社会里,我们对画的标准影响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普通观众,他们衡量艺术的标准已经变成了画市上的价钱了,但市场的价钱充满了虚假。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真正影响或者腐蚀了我们的画家,使画家没有为精神工作的纯粹性了,他失去了艺术家的本质和气质。就像我写的洛夫这样的人,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家,但是他们被市场收买,最终又被市场抛弃。
尽管近二十年我一直在田野奔跑,在做古村落的抢救,非遗的抢救,但是我相当一部分的目光注视着艺术界,我也注视着作家们,我有时候有忧患。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没有出现80年代罗中立画的《父亲》那样的作品。因为我们的时代缺了80年代艺术家的纯粹性,以及对时代的激情。
南都:《艺术家们》里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中国艺术家群像。您觉得哪个人物是写起来最艰难,最耗心力的?哪个人物是您个人最喜爱的?
冯骥才:实际上,如果我像写楚云天这么写高宇奇这个人物,肯定是很难写好的。因为我是从楚云天的角度去写的,小说里最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或者我最崇尚的人物,或者楚云天最崇尚的人物,实际是两个人,一个是高宇奇,一个是易了然。我都没有把他们放在楚云天的身边,不像罗潜和洛夫。这两个人没有和楚云天生活在一起。我把他们放在远处,一个在安徽,一个在河南。
因为我觉得,只有放得远了,有距离了,这个人物才能更理想化。
好多人知道高宇奇的生活原型是李伯安。实际上,我在写小说的时候,跟我现在对李伯安的感觉是一样的。在我心里,李伯安就是一个神。
我跟李伯安的故事可能你也知道,关于李伯安的第一篇文章《永恒的震撼》是我写的。我认为,如果说20世纪前半个世纪最伟大的画是蒋兆和的《流民图》,后半个世纪最伟大的画应该是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它是永远留在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幅画。这个画家最了不起的是,他一生从来没有卖过一张画。价格不是衡量他的画的标准,衡量他的标准是一个时代的艺术,是我们心里崇高的审美。
我的文化遗产抢救不是学者立场,是作家立场
南都:对于当代的艺术界来说,凝聚了您一生感悟的《艺术家们》可以说是一部批判和警示之书。小说出版以后,在艺术界是否引起反响?您是否希望它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功能?
冯骥才:当然我也听到艺术家们有很多的议论。我担心人们会以为我的某一个人物是在影射某一个画家,但目前还没有这种情况。
但是大家也在思考,一个是高宇奇这个人物,另一个是艺术家们对价格的追求,导致当前的艺术明星都是价格最高的。过去我们一说好的画家应该是吴作人、徐悲鸿、李苦禅,他们的画艺很高,我们不谈他们的价钱。现在一谈画都谈价格,都为一张画过了亿感到惊讶。
人还在世,一张纸才六尺长,你画完一张画比一个工厂的价格还高,怎么可能呢?这其中就有很多商业炒作。我觉得这个小说引起的这方面的反思比较多。
这个小说实际上我还没写完。我刚写完了一个中短篇的小说集。明年找时间,我还要写一个艺术家的小说。我觉得它有两重意义,一个意义是艺术家的主题,另一个意义是我所在的这座城市的主题。
天津这座城市跟其他城市是不一样的。它有两半儿,一半儿是老城,我写的《俗世奇人》《神鞭》《三寸金莲》这些小说发生在老城。它有独特的地域个性,水陆码头,市井风气很浓,而且这些地方全说天津话。这是一个天津。还有一个天津是租界里的天津。租界里的天津华洋杂处,做洋务的人比较多,全国各地来的富豪比较多,这个地方跟上海的英法租界有接近之处。
写完了《俗世奇人》,我觉得我把老城不同的人的性格、地域的特点、地方人的逞强好胜基本上都已经写得差不多了。我是在租界里长大的,这块土地给我的生命影响很深。如果今后我还能写,我想好好地写一两部书,体现租界这个地方独有的文化气质。
南都:您在《艺术家们》的前言里说“要用另一套笔墨写另一群人物和另一种生活”,是否也和艺术家们的故事发生在租界而非老城有关?这部小说使用的笔墨和《俗世奇人》相比有什么不同?
冯骥才:有的作家就是有好几套笔墨,有两套笔墨的作家很多。比如说鲁迅,鲁迅写《阿Q正传》《狂人日记》,还有他的杂文是一套笔墨,是鲁迅的笔墨。鲁迅写《伤逝》,写《祥林嫂》是另外一套笔墨,味道是不一样的。罗曼·罗兰写《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套笔墨,他写《哥拉·布勒尼翁》用的是另一套笔墨。有的作家用一套笔墨写所有的东西,有的作家就是两套笔墨。
我一直是两套笔墨,可能跟我独特的生长经历有关系。租界人的气质跟老城的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租界,在一个洋场环境里生存的文化,跟地道的、乡土的、码头的生存文化是不一样的,人的集体性格也不一样。所以我想,写两个地方,用两套笔墨,更契合这片土地的独特气质和韵味。
另外,在文字的运用上有不同的审美,写作也是一种快乐。《艺术家们》的文笔和《俗世奇人》完全不一样。比如说,《艺术家们》里有大量的散文化的东西,比如我写到美,写到环境,写到抒情,就有大量的散文。《俗世奇人》里绝对没有散文。《俗世奇人》里更多的还是中国传统笔墨,比如《三言二拍》,比如中国的口头文学,笔记小说,更多这样的东西。
南都:自上世纪90年代起,您将大量时间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二十年后,您再度“回归”文学,推出了《单筒望远镜》《俗世奇人全本》《艺术家们》等引发广泛关注的作品。您觉得现在的您在观念上、技巧上、心境上和80年代蜚声文坛的您有何不同之处?您对未来的创作还有什么期待?
冯骥才:我很有意思,我的文化遗产抢救不是学者立场,是作家立场。我是在最好的时候,90年代初,笔最热的时候,转向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因为作家嘛,你受恩于生你养你这块土地,你一定要把这块土地的灵魂,你对这块土地的情感,还有对生活本身的认识写出来。
可是你太热爱这块土地的时候,当这块土地上的一些文化、一些历史的遗产、一些历史的精神与文化财富在时代变化中逐渐濒危,受到损失,有的快要消亡的时候,你不可能不出来保护它。就像你自己的母亲受到了伤害,你就要保护它。
我是出于作家的立场来做的文化遗产保护。做了二十多年,一直做到本世纪20年代,这时候我自己体力不行了,往田野跑得少了,在书房里的时间多了,我25年左右做文化遗产积累对大地的理解,对地域性和个性的理解,对土地上人们的文化和人们独特性格的理解要比以前深刻得多。二十多年的积累对人的命运、对社会的认识,包括要爱和要批评的东西,也要多得多,这个东西后来反过来又促使我写作。
现在写作,文本方法我就不细说了,我觉得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心里面还有东西要写。我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我曾经有一次对记者说过这么一句话,不是我找的文学,是文学找我来了。我过去知道的同时代的艺术家,我要是不写,谁也不知道他们。他们找我,就要让我写。
我不敢给我自己派的活儿太多。因为我现在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还有些事情要做。国家几个遗产保护中心都在我的大学里边,像古村落保护中心、口述史中心、木版年画中心……我直接要负责这些工作。还有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另外,从今年开始,我们创建了非遗学的学科硕士点。还有大量的教学培养规划、教材的编写等。所以我现在把画画停了。现在我写作肯定要写。而且正在写。文学创作对于我是不可遏制的。(采访/南都记者黄茜)
编辑:刘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