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作者所言,“晚熟是一种对于人物成熟的精神和心理状态的描述,以及对于自己源源不断的创新的期盼。”相比起莫言过去那种具有强烈倾诉色彩的呐喊,《晚熟的人》则将其叙述或回忆的所有内容都落实在当下的时刻中,呈现出莫言对于时代变迁中复杂社会的迟疑、思考和价值立场。
莫言的新作《晚熟的人》可以说除《贼指花》与《天下太平》以外,其余的短篇小说都运用到了知识分子“还乡”的视角,描写了家乡中平凡的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中的日常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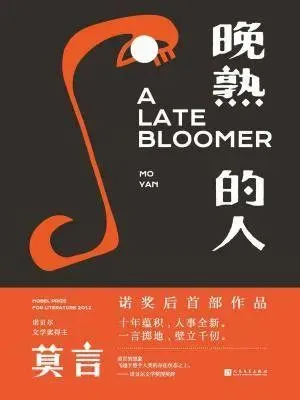
在看完这本小说集后,我首先想起的是另一位作家鲁迅。我认为无论是小说的知识分子还乡的视角,还是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一些相似之处。如《红唇绿嘴》中的高参的出场方式,就与《故乡》的杨二嫂极为相近,当然这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人物,但蛮不讲理的本性倒是有几分相像。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莫言对鲁迅先生的致敬,也可以看到莫言在还乡书写中对自己、故乡与时代变迁的审问与思考。
在这里,我以鲁迅的《故乡》和《晚熟的人》为例,尝试将二者进行对读。鲁迅笔下的故乡是与封建传统的陋习、前现代的愚昧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故乡呈现出的是麻木的国民劣根性,充斥着一种现实主义色彩的悲剧意味。同时,鲁迅建构了一个与现实故乡相对立的理想故乡,存在于鲁迅回忆中的理想的故乡民风质朴、融洽协调,与现实中的破败与闭塞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当“我”这一个积极而奋进的知识分子返回故乡,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一种“启蒙者的孤独与悲哀”。而在莫言的笔下,无论是回忆中的故乡,还是现实中的故乡,都充满着暴力、冤屈、伤痕和悲剧。但是与以往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乡书写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莫言以沉着、冷静、理性的笔触叙述了他的返乡经历,描绘了现代化社会裹挟下各色各样的小人物,也呈现出他鲜明的道德立场。与鲁迅笔下人物的悲悯与绝望不同,《晚熟的人》中的人物都呈现出一种生命的韧性——在厄运的折磨中有韧性地挣扎。有的人带着伤痕安分地度过余生,如《左镰》中的田奎在被“诬陷”的暴力惩罚中失去了右手,但他变得什么也不怕,只愿讨得一个有过两段婚姻的女子安安分分地过日子。有的人带着生存的冤屈奋力反抗,如《斗士》中的武功心生屈辱,一辈子都在与人斗争,“跟谁没完”,并凭借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斗争精神活到最后。有的人做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挣扎与反抗,如《表弟宁塞叶》。在这种挣扎与反抗中,也包含着面对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的被迫沉沦,如《澡堂与红床》中的白牙姑娘。
可以看到,《晚熟的人》与莫言过去的写作有所不同,可以说是莫言获奖以来的一次新的尝试。这一次,莫言并没有站在高处对故乡中各色各样的小人物进行批判,或者说相比以往,《晚熟的人》批判性有所减弱,但作者依旧保持着对过往时代进行理智的审视的分析。从这个角度而言,便呼应了题目《晚熟的人》,正如作者所言,“晚熟是一种对于人物成熟的精神和心理状态的描述,以及对于自己源源不断的创新的期盼。”相比起莫言过去那种具有强烈倾诉色彩的呐喊,《晚熟的人》则将其叙述或回忆的所有内容都落实在当下的时刻中,呈现出莫言对于时代变迁中复杂社会的迟疑、思考和价值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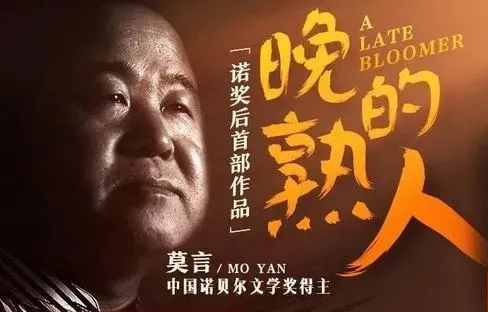
最后,还想单独谈一谈小说《红唇绿嘴》。《红唇绿嘴》中的“高参”对莫言的歇斯底里的攻击和软磨硬泡,使我想起朋友圈中看到的一则诈骗信息。
当时是我的一位朋友接到了诈骗的电话,对方假装自己是美团的客服,然后说出朋友的个人详细信息,包括地址、电话、毕业院校。一般来说,这些被泄露的个人信息成为他们诈骗的重要诱饵,当你的个人信息被陌生人完完整整地说出来,你或许就会迷迷糊糊地相信他就是美团的客服。只要你相信,诈骗也就接近成功了。
然而,这位朋友直接和骗子杠上了。
她问骗子:“你年纪轻轻干个遵纪守法的工作不好吗?”
骗子说:“难道让我去当个保安销售一个月那么几千块钱吗?”
友人:“那你这样骗人就好吗?”
骗子:“难道我要在家里游手好闲吗?”
友人:“你知不知道做坏事会遭报应?”
骗子:“你怎么这么迷信,快吃饭了,我不想破坏吃饭的心情。”
原本我们都以为这件事情结束了,然而这个故事是有后续的。当天的下午,骗子的同伙又给我朋友打了一个电话,问她:“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说我干话务员的同事没有前途?”我朋友还没反应过来,骗子便接着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同事上午打了电话给你以后就不想干了,想回家。我也想回家,你也来劝劝我。”(我猜测他的语气略带讥讽。)
友人:“你想回家就回吧,还用我劝?”(多少是有点不耐烦和莫名其妙了。)
他说:“大哥!我们现在在国外,在泰国!你觉得中国好?”
友人:“中国不好吗?我觉得中国特别好,我没出过国我也觉得中国好。”
同伙略带讥讽地说:“哦!你没出过国啊,那打扰了,我和我们这边的人后续不会再给你打电话了,再见!”
和小说中的“高参”一样,现实中的骗子也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稳固”的心理建设,他们并不在意别人对他们的不解和劝导,而坚定地往自己设定的方向继续错下去。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固执和执着!
这些驻扎在异国他乡的“假人”,既不甘于做普通的打工人,也不相信普通蓝领工人的生活前景,沉迷于生财有道。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说是底层打工者精神与物质层面的双重空缺。这些“晚熟的人”自以为占据着智商的高地,借以谎言和谣言贪婪钱财。在金钱面前,仁义道德皆为粪土,于是陷入一种几近疯狂的状态中。
本文作者焦糖花,中山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在读,喜好读书和养生,大型犬只爱好者,居安思危冲刺型选手。
来源:读书郎闲笔微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