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女人个个相似,不幸的女人各各不同。”这句话源自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一书,只不过我把“家庭”改为“女人”了。所以如此,主要是这两天的所见所闻,让我感慨万千。
前天是“三八”妇女节,网上涌现大量祝福女同胞的图文和视频,有说“三八节快乐”的,有称“女神节快乐”的,还有喊“女王节快乐”的。至于女同胞与亲朋外出游玩、品尝美食等等的“现场播报”更到处可见。其中有一个短视频比较搞笑,说几天前某单位发出“通知”:今年“三八节”女同志依例放假半天。但因为前天是星期六,所以该“通知”遭到众多网民特别是女同胞嘲笑。有人借此提出:各地各单位应给妇女们补休半天假。居然得到浪涛拍岸般响应。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如今我国妇女的地位高得确实不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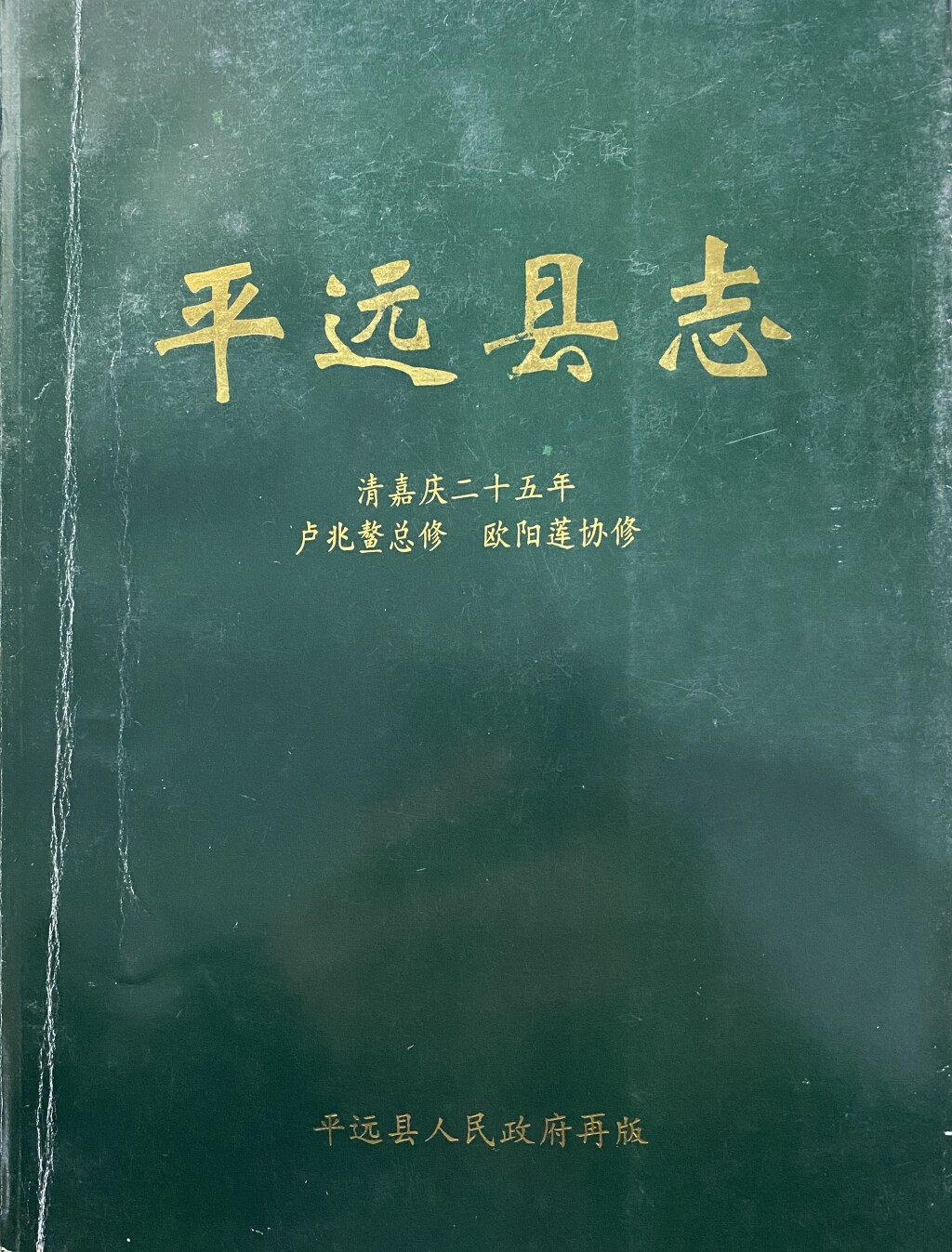
嘉庆二十五年版《平远县志》(2012年整理再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代客家妇女乃至全国妇女的景况:很多时候——特别是明清时期只能用一个“惨”字来形容。为何这般言说?主因是这两天我偶然翻出了清嘉庆二十五年版的《平远县志》,一不留神读到了卷之四的“列女”和卷之五的“列女(续编)”,不禁被其中一条条记录惊呆了!以前不是没听过或看过关于古代妇女守节如何悲惨的故事,也不是没看过五四运动时期反封建先驱们的言论,譬如鲁迅先生的“‘吃人’说”,但是,直到我在这本县志中读到原始记录时,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人间惨剧,什么叫“于我心有戚戚焉”!
这部《平远县志》是平远县政府于2012年组织整理后再版的。它记载了该县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设县起至十九世纪初期“在自然、地理、历史、沿革、经济、文化、社会风俗、人文等各方面状况”,“列女”及其“续编”并未置于“人物”系列之中,而是单列出来以示重视的。(说明:“列女”也称“烈女”。民国以来有众多专家论证过前者是如何转变为后者的。在此不赘述。以下以正史为本,仍用“列女”。)据查,自西汉刘向创编《列女传》,得到正史《后汉书》响应单列《列女传》后,历代众多官方正史(《二十四史》有一半)和地方志均“援以为例”。《平远县志》亦如此。在整部县志中,《列女》及“续编”共70页,篇幅规模居各版块前三;共记录了小至8岁大至40多岁的551名列女事迹及所获荣誉等,其中“正编”194名,“续编”357名;列入“正编”者有长则数百字、短则百来字的叙事和评介等,而列入“续编”的只有姓氏、地址、夫名、年龄、守节原因及时长等寥寥二三十字。550多人中,除个别在修志时(1820年)仍活着外,绝大多数已亡故;生卒年月全部阙如;而且,除一个叫“韩秀姑”的外,都只有姓无名字——标准格式是:“某氏 某某某妻或某某某女。”男尊女卑得无以复加!如果不是想了解各位列女的具体言行,我早把这破县志丢到垃圾堆去了。当然,《平远县志》也不能说是坏书,但它封建腐朽味实在太浓重了!幸而其所记史实大都有根有据,故尚有其价值。
它记录了列女们的“嘉言㦤行”。在今人看来其实多为惨状——
身份:绝大多数是寡妇。如果再细分,则大多为正妻,亦有继室(即填房),还有妾。如,陈氏,“生员姚昊继室。年十六归昊。昊先举一子矣。氏有子二,昊殁,誓守节,遇嫡子如己子。”(“遇”指“对待”)又如,蓝氏,“石正王才用侧室。才用在家娶室卓氏,未生子。随往江右(指江西)贸易,娶氏为妾,生二子于江右,置立产业。未几,才用故。氏年二十七,矢志孀守。留次子在江右,守其产业;携长子回籍承祀,艰苦备尝。”这个蓝氏是修县志时仍活着者之一:“现年九十岁。子若孙得列衣冠。”(“若”为“和”“与”义。)
寡妇们“寡”的状况不尽相同。绝大多数是嫁入夫家后丈夫因各种原因死了,其中有的生有儿女,有的则没有。也有的嫁入门了,但未圆房男人便病夭了,如林氏,“东石吴敏学妻。年十六于归,因夫病笃,未谐伉俪。距五日,夫故。”还有一些是“望门寡”,即定了亲但还没嫁过去名义上的丈夫就死了,如杨氏,“黄畲杨公荣之女。自幼许字韩毓通。十四岁,通故。氏誓不他适。”还有上文提到的韩秀姑,“许字卓文琦,未嫁,琦没。时氏年十七……”——至于为何550多名列女中只有她留下了全名,我研究县志多遍均未获头绪!据估计,她也可能是明清两朝全国众多列女中极少数留有姓名者之一。
平远550多名妇女之所以能县志“题姓”,原因或说“理由”众多。先说说属于极少数的非寡妇者:具体几个因县志记叙不清晰难以统计,但至少有三人之死是与贼乱有关的。一为陈氏,“小柘蓝可望妻。被贼掠。贼露刃,挟以行。遇道旁树,辄(立即)以手坚抱。贼怜其貌,初不忍杀。氏抱树愈坚,且詈且泣。贼怒斫其颈,血流满地,犹骂不绝口。”另一为吴氏,“畲脑张士统妻。顺治庚子避贼,遇游兵,见其少,欲掠之。氏惧受辱,跳水死。”还有一位是张氏,“石窟人。适长田马骆。避乱山寨,寨将破,授一子与夫,曰:‘与君永诀矣!’遂自缢死。”这三位死得都很壮烈,尤其是陈氏,古人说“大丈夫刀斧加身而不惧”,陈氏亦可称“大丈夫”矣!
再来看看其他妇女:
有自杀殉夫的。如,何氏,“升福人。年十六适吴日际。才七月,夫卒。氏不欲生,母与姑严卫之。哭踊绝食。夫盖棺后,潜入室自经。”才16岁的小姑娘,结婚7个月丈夫就病死了,虽然母亲和婆婆(姑,《尔雅·释亲》:“夫之母为姑。”)严防死守,她还是偷偷上吊(自经)死了。再如,钟氏,“超竹人。适长田邱以进。氏归宁(回娘家),夫闻寇至,惊心闺壶(女子居所,借指钟氏),往超竹,途遇寇,执以进至热水,杀之。氏闻夫变,辄经于厕。姑妹救之得苏,不食,五日,自缢于床下。”此钟姓女子听到丈夫遇害后马上上吊(经),被救后绝食5天,最后吊死在床下面。其死志之决绝,实在令人惊愕又心痛!像这类夫死就自杀身亡的在县志中还有不少——有的还蛮特别,让人哭笑不得:譬如,林氏,“东石刘显祖妻。生员林隽女。适刘二年,而显祖病笃,与林诀曰:‘汝(你)年幼,当别适(改嫁)。’氏含泪谢之,即服药死。显祖后病愈。”就是说,不该死的吃药死了,该死的却病好了!这叫什么事啊?
有为子嗣或伺奉公婆而活着或不改嫁的。这类人最多。怀着老公骨血而放弃殉夫的有好几个,如姚氏,“林英仕妻。年十七,夫病不起,欲自缢。俄(不久)抆泪告姑曰:‘妇有遗腹一月,未敢轻死。’后果生男,截发孀居,贞洁自守。寿八十有四。”必须抚孤而活着的更多,如凌氏,“陈才颖妻。年十七归才。生子尚襁褓而才卒。时当变乱,有觊其产业者欲迫之嫁。氏归母家,矢志守贞;篝灯课子,备历险阻,以全节终。”为伺奉公婆而苟活的也不少,如张氏,“职监韩揆甲妻。姑患目及瘫。氏虽富户女,念姑老且病,饮食亲自护持,床褥衣衾亲手浣浣(洗涤),绝不假手女奴及子妇辈。姑病卧十三年,氏未尝一日离左右。”富家女能如此,凿实不易!还有一人更牛:姚氏,“诸生凌灵芍妻。姑耄,齿落尽,不粒食,氏乳之三年。”就是说凌灵芍的母亲八九十岁了,牙齿全掉吃不了米饭等物,于是凌妻就以自己的奶喂家婆吃了三年!还有抚孤与事亲一肩挑的,如李氏,“刘淑超母。夫丧,遗孤一岁耳;翁姑且老。氏誓抚孤事亲孀守,数十年如一日。”这些都属于当代可以理解的范围;有的则让人感到不知所谓了,如萧氏,“徐润斯妻。年二十二生一子,徐殁,子殇。人谓‘而(你)无子何守为?’氏曰:‘吾夫儒林也,奈何辱之!’”居然只是为了不辱没亡夫读书人的脸面而不再嫁!别人看了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我想不通!

梅州市现存的天褒节孝石牌坊(坐落在蕉岭县蓝坊镇),建于清道光三年(1823)。
列女们守节时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大多值得肯定。最多的是克服穷困养活家人的。譬如,耕种纺绩的:姚氏,“凌先连妻。连殁,氏年未及笄(不足15岁)。家贫,数饥馁,氏绩纺哺孤,数十年不渝。”再如,外出当佣工的:张氏,“萧运谋妻。运死,遗子元宁。家贫甚,人劝之嫁,氏曰:‘饿死,事极小耳。’乃称未亡人,为佣菜以活子,历久不渝。”又如,挖野菜的:韩氏,“俞兆桢妻。夫殁,遗二孤。姑亦寡,家极贫。韩掘蕨(一种野生草本植物)抚哺。人曰:‘何辛苦为!’韩曰:‘吾岂怕寒饿死者?’”如此种种,莫可胜记。还有不少是不仅对子女、翁姑好,还善待丈夫前妻子女、丈夫兄弟、妯娌、下人甚至邻人的。如,李氏,“大柘即用吏目林昌琼继室……琼年艾七(57岁)而终,时氏二十九岁,冰霜自矢,抚琼前妻子如己子,辛勤课督……”。再如,张氏,“豪居从九黄清瑞妻。年十九适清;二十七,清宦殁旅次……善事堂上人(年长家人),抚孤业孺,克底成立后,姑年登耄耋,氏夫兄弟四人俱先故,氏皆为经营葬祭。”丈夫的四个兄弟死了其后事均由张氏张罗了却。所谓“长嫂如母”,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又如,刘氏,“差干谢毓麟妻。年二十三,夫故……遇邻人贫乏,频加周恤。”更可敬的还有捐资或田地兴学助困的,如,邱氏,“黄畲杨震光妻。年二十二夫亡……命其子捐金以修文庙,施田以助文会。”此外,还有宁愿自己过苦日子也把丈夫遗留的“三百金”悉数分给夫家“兄弟与族之贫者”的赖氏(东石林显枢妻)、分家时“情愿少受”财物的姚氏(大柘儒士林孟达妻)、“处妯娌诟谇不形”(被妯娌辱骂不怒形于色)的余氏(东石刘如监妻)、“烹茶以便行人”的钟氏(大柘姚在亁妻),如此等等,言行都相当高尚。对比当下,有些事今人也未必能做得到——譬如分家不仅不争钱财还情愿少拿。
不过,“节妇”也有行为过于激烈让人难以接受的。除上面讲到的自杀以外,还有“断右手中指,自矢守节”的(韩氏,生员邱世基妻),“毁容,示不嫁”的(蓝氏,曾友忠妻),以及“望门寡”却主动跑到亡夫家“替夫尽孝”的(如上面提到的韩秀姑)……
也许有人会问,列女们守节不苦吗?当然苦!除了竭力劳作维持生计、照顾家人外,为不给人讲闲话,有的“守志数十年,未尝见启齿笑语”(钟氏,庠生林运随妻),或“见宗党子弟辄避去,绝不闻笑语声”(袁氏,全其俊妻);有的婆媳“麻帐宵灯,凄其共守”(陈氏和姚氏,陈氏为石正谢碧妻,姚氏为其儿媳妇);有的数十年“足迹不出闺门,姻戚罕靓其面”(林氏,大柘儒士姚生售妻)……
有时候我真想不明白,这些“节妇们”究竟中了封建思想多深的毒才会有此等言行!然而,这都是历史上在我老家真真切切发生过的。由此,当我看到县志中一个个旌赞之语如“松心柏节”“兰芬湘洁”“德节兼优”等就心生厌恶,同时不能不对传统礼教特别是宋明理学生出无穷憎恨来!
虽然守节很苦很惨,但偶尔也有“意外之喜”。譬如,吴氏,生员林运甲妻,林殁后,她与8岁的儿子一起随家公“赴句容县任”,船过扬子江时,“子忽坠水”,她以为儿子肯定没救了,觉得万分对不起亡夫,于是跳水自尽,谁知,“甫入水,如有物负之者,母子牵裾出,得不死。”此结果谁能想得到呢?还有一个更不可思议——这也是县志中记述列女事迹文字最长的一个,故事梗概为:张氏,“小柘人。劭年(少年)许配李某为妻。李父丧,家贫,往台湾佣工,日久未归。氏父贪金,欲另择配。氏坚执不从,年已二十四。父受富户聘资,强迫改适。”张氏依然不从,并在李某邻居帮助下,私自跑到李家为媳。李家长者开始不答应,说:“我一贫如洗,不能养赡,若何?”张氏回答:“婿归,我为李家媳;婿不归,我为李家儿。愿孝死养姑……”留在李家后,她还经历许多波折,直到“五十余岁矣”,李某竟然回来了!于是欢天喜地“行合卺礼”,“后乃连举(生)二子。”你说神奇不神奇?守了二三十年,不但守到云开见月明——丈夫回来了,而且五十多岁了还连生两子!如果不是县志所载,大家都会把它当小说家言看。
站在修志人立场看,对“节妇们”无论是给予旌表也好,立贞节牌坊也好,或者称颂吴氏、李氏这种“福报”也好,无不是倡导“正确思想观念”的高明办法。但是,也正是这种成百上千年的倡导甚至强迫,才使广大妇女中毒入骨,以至于从“别人要我这么做”变成了“我必须这么做”,形成从思想到行动的“自觉”。这充分彰显封建意识形态是多么可怕!
幸运的是,当代妇女再也不用受封建礼教束缚和压迫了。不过,在我们欢庆“三八节”的同时必须警惕:现在社会上是否还存在某些类似的封建余毒呢?它们会否成为我国阔步迈向现代化的阻碍呢?但愿我的忧虑是完全多余的!
——姚燕永@粤东野语










